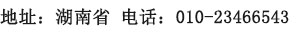北京时间11月9日在美国获批进入当地医药市场的呋喹替尼,在48小时内已开出首张处方,成为首个在海外开出处方的上海原创新药。这是最近十多年美国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小分子药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肠癌是全球发病率第三、死亡率第二的常见癌症。
就在上个月,另一家上海企业君实生物研发的特瑞普利单抗,成为我国首个在美国获批上市的自研自产创新生物药,填补了美国鼻咽癌的治疗空白。
远看全国,最近十年有个由国内企业研发上市的创新药,占全球上市创新药的15%,在研创新药占全球的33%,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一些药企的原创新药,在海外申请上市接连遇挫。
近看上海,生物医药企业“接一连二”扬帆“出海”。进入美国医药市场,究竟有何意义?这对于上海乃至国内其他药企的“出海”之路,有何启示?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在上海张江一家咖啡厅的餐巾纸上,画下了呋喹替尼最初的小分子结构。这一年是年,当时的张江乃至中国,从事新药研发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甚至鲜有人去谈论创新药,仿制药才是主流。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新药平均需要长达十年、多达十亿美元的投入,且“九死一生”。当时的全球新药研发格局中,美国“一骑绝尘”,欧盟和日本位列第二梯队。
做仿制药还是创新药?
和黄医药选择了后者,因为仿制药只能在国外原研药专利失效后做,这样我国患者就无法第一时间用上好药。
君实生物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PD(程序性死亡因子)-1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现,堪称人类抗癌史上的重要事件,年国外开始启动PD-1临床试验,这些触发了几位年轻科学家的念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中国人自己的抗体新药?年他们在“张江药谷”孵化器一个不到平方米的租赁空间成立了君实生物,并很快在美国也建立了研发中心。
两家企业的选择为“出海”埋下了“伏笔”。因为在美国医药市场上市,首要的是能够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有差异化的创新药有着仿制药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今,和黄医药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0%,居中国创新药企榜首。君实生物的研发团队也有上千人。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两家企业都受惠于年我国启动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与此同时,这也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对中国创新药的